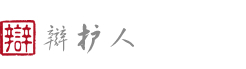毕祺祺前往淅川法院递交辩护手续
▍作者 邓庆文
▍来源 公众号辩护人Defenders
近日,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法院对法官毕祺祺担任母亲辩护人的申请保持沉默,与七年前江苏法官家属辩护遭拒事件形成刺眼的时空镜像。当法袍之下的司法从业者都难以兑现辩护权,这场法治困局暴露出更深层的司法生态病灶。
一、法律明文下的"隐形门槛"
刑诉法第三十三条如同阳光下的明镜,清晰映照出公民辩护权的法定边界。法律既未设定"职业回避"条款,也未对辩护人身份设置职业壁垒,法官家属担任辩护人本应畅通无阻。然而淅川法院的"冷处理"策略,却在法律文本之外构筑起无形的玻璃幕墙。这种以不作为消解法律效力的行政惯性,本质上是对程序正义的慢性绞杀。
在江苏某副市长受贿案中,法院以"可能影响审判公正"为由拒绝法官妻子辩护,已然暴露出司法系统对亲属辩护权的认知偏差。这种将职业身份与辩护资格混为一谈的逻辑,恰如担心医生家属生病会破坏医疗秩序般荒谬。当法律人的专业素养遭到制度性怀疑,司法系统正在经历严重的自我认同危机。
二、权力谱系中的司法异化
淅川法院的沉默与江苏法院的明拒,共同指向司法随意化的沉疴。在县域司法生态中,法官不仅是法律适用者,更是权力网络中的节点。当案件涉及系统内部人员,审批流程便自动触发"风险管控"机制。这种将法律问题政治化的处理方式,实质是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原则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溃败。
司法系统内部形成的"潜规则体系",正在消解法律的确定性。辩护权行使异化为权力博弈的筹码,法定权利沦为可有可无的器物。当法院对同类案件采取差别化处理标准时,不仅摧毁公众的法治信仰,更在司法肌体内部培育出选择性执法的毒瘤。
三、破局之路:从制度突围到理念重构
破解困局需双管齐下。一是在制度层面建立侵害亲属辩护权的追责机制,将否决理由纳入法定评价框架;二是在理念层面重塑法律职业共同体意识,消除"体制内回避"的认知误区。最高人民法院可通过指导性案例明确裁判规则,将纸面权利转化为可操作可救济的诉讼程序。
当"法官为母辩护"不再成为司法系统的道德困境,当职业身份不再构成权利行使的障碍,司法改革才算真正触及灵魂。
法律人的家属辩护权困境,恰似司法改革进程中的压力测试。它既检验着制度弹性,更丈量着法治文明的刻度。当司法系统能够坦然接受内部人员的依法辩护,法治才能真正完成从文本到实践的惊险一跃。期待这场关于辩护权的博弈,能够推动中国司法走出随意化泥淖,在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的平衡中重拾公信。


| 上一篇: 仲若辛丨多收三五斗 少判三五年 |
| 下一篇: 苍南法院违法剥夺被害人诉讼权利:程序正义的溃堤之险 |